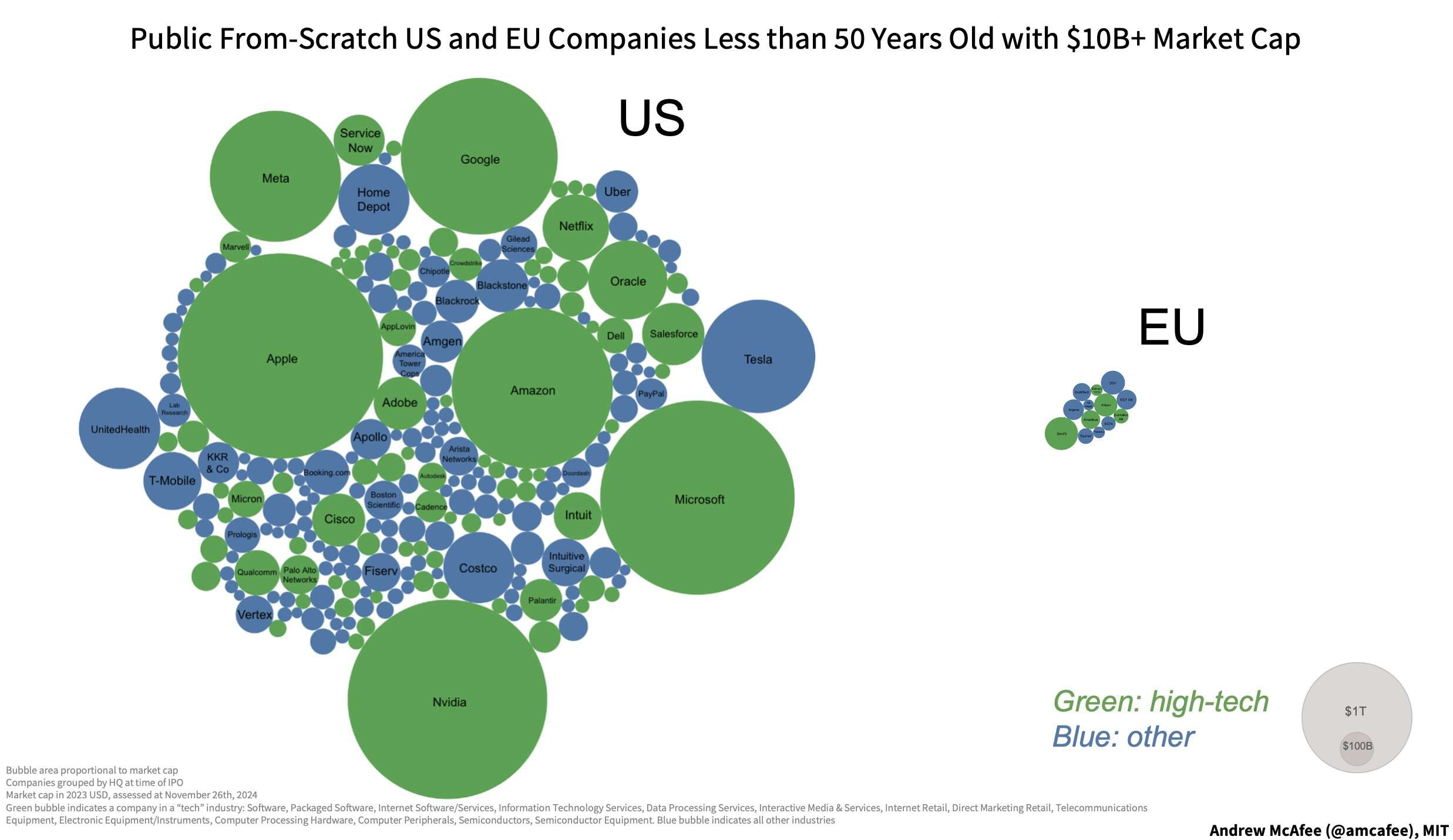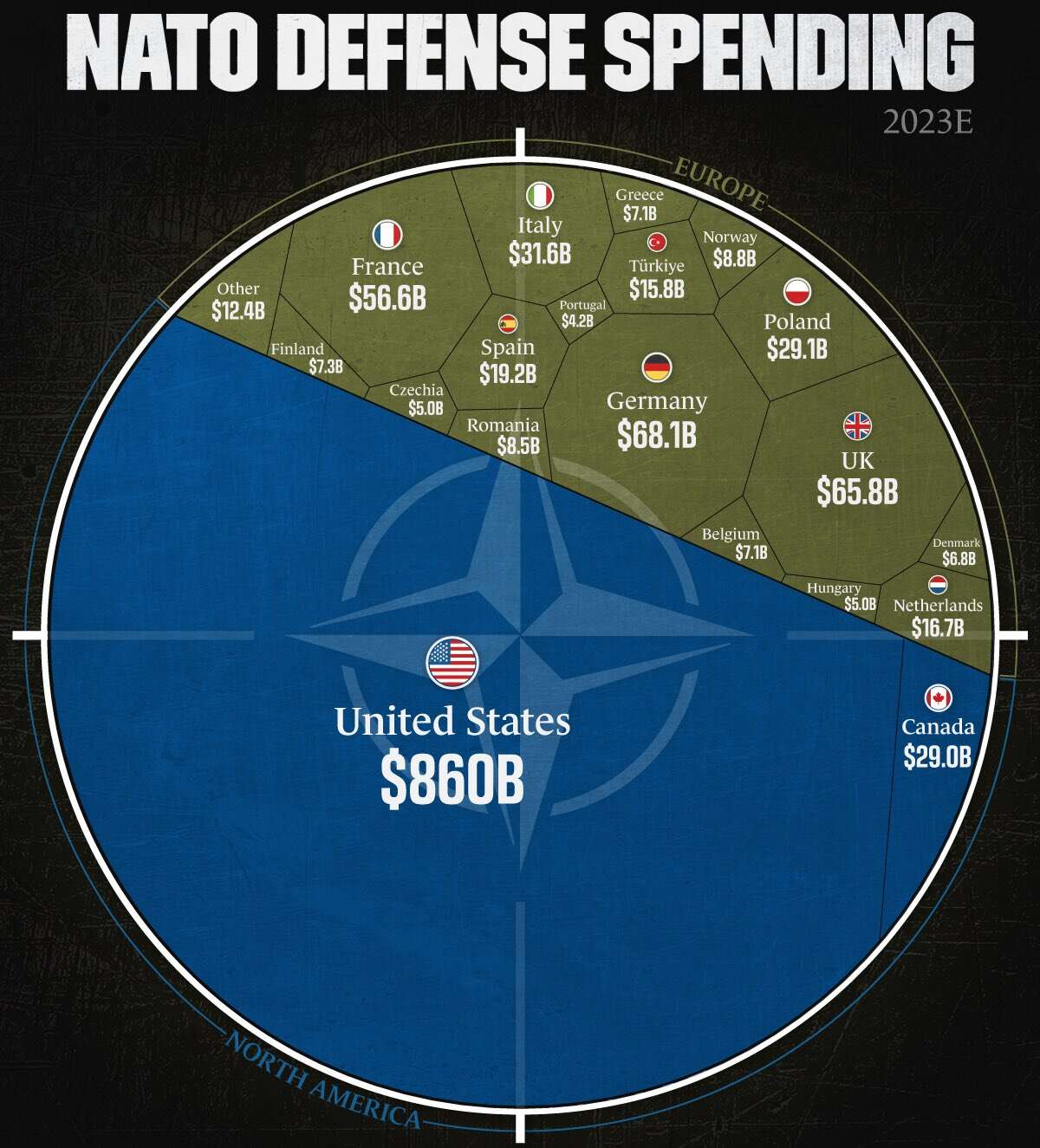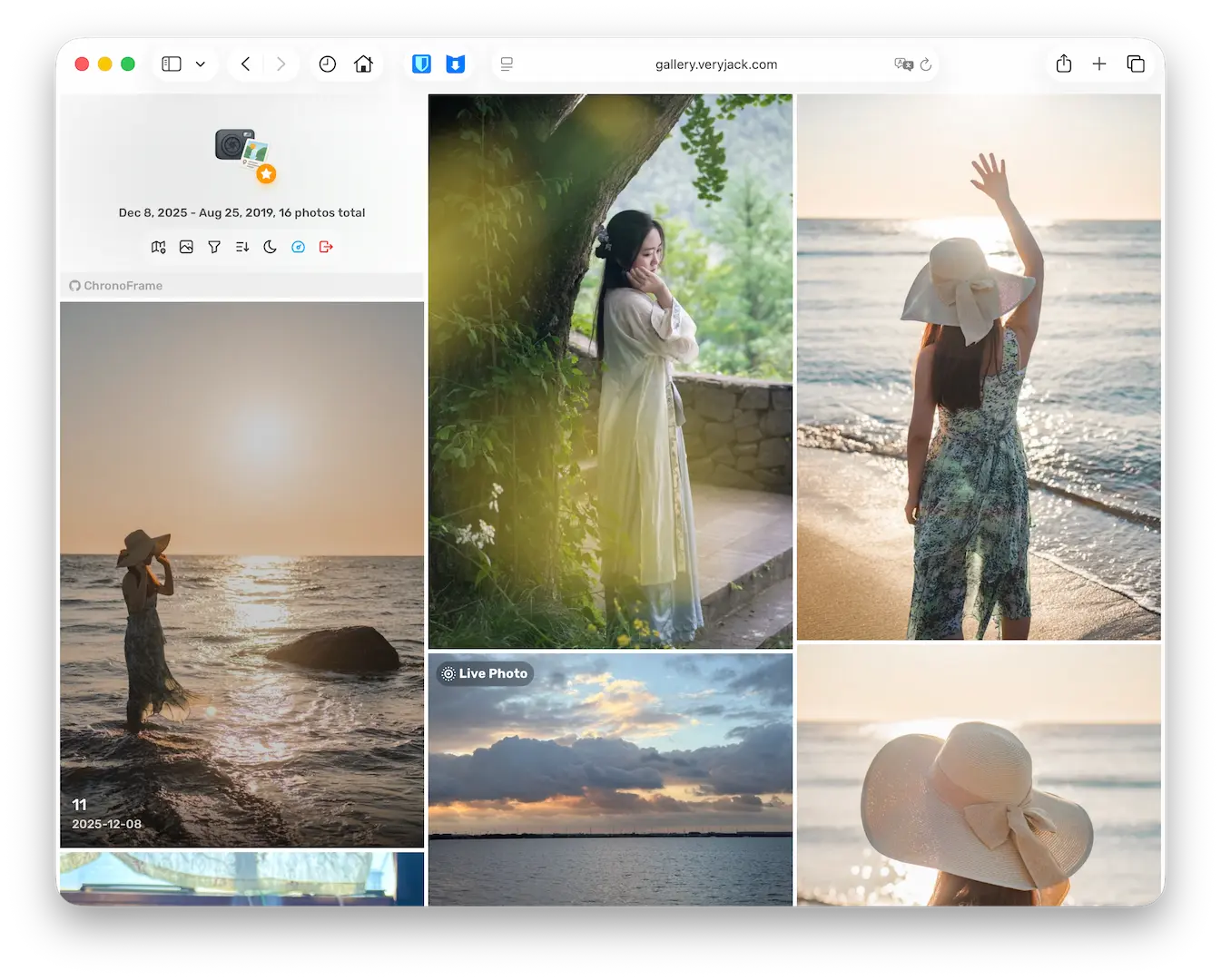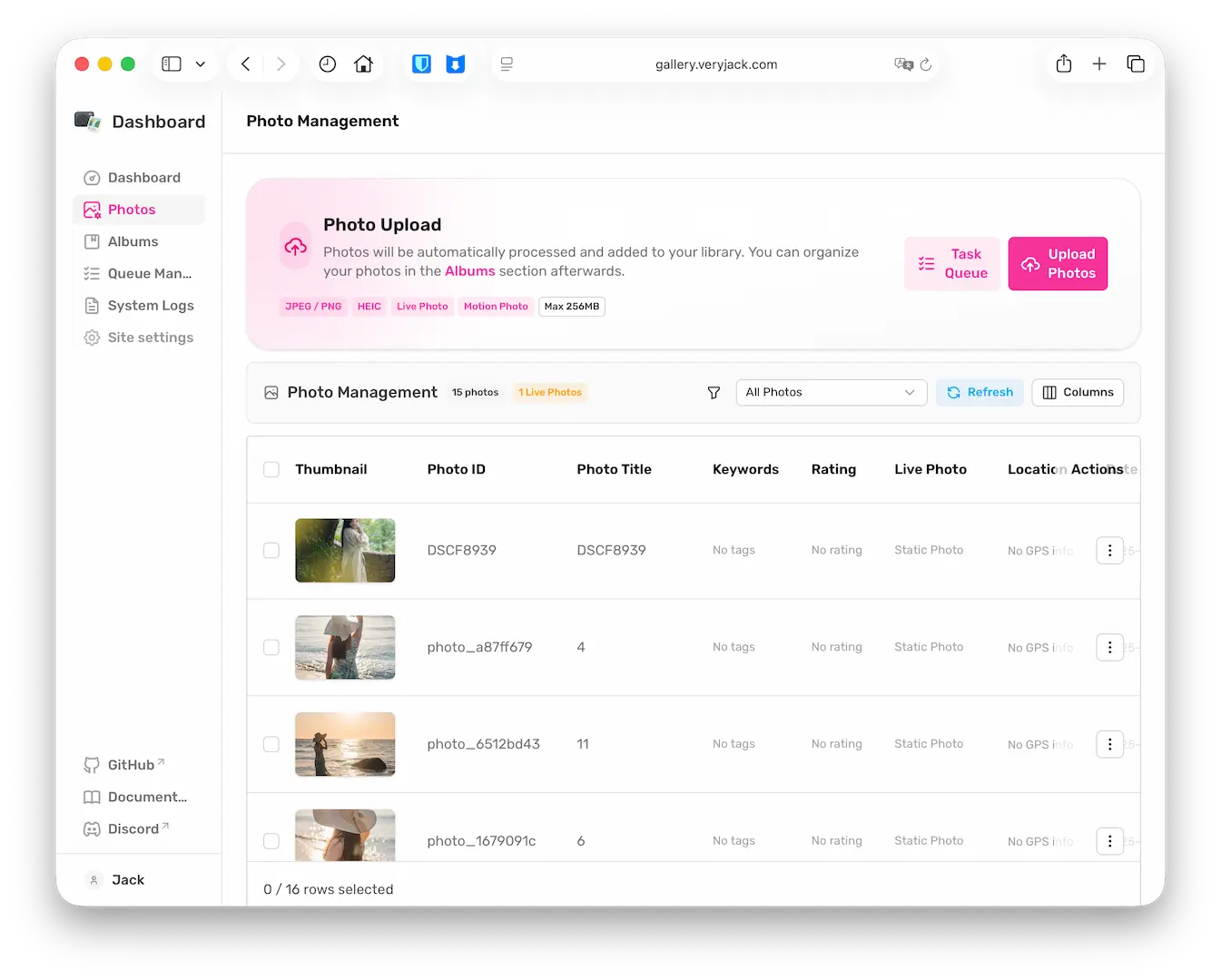论哈特对奥斯丁的栽赃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的一个问题出发点是,人们通常认为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但又不明白社会拥有一个规则意味着什么。
奥斯丁的主权者命令说中的“主权者”恰好又其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被其他成员习惯地服从却不习惯地服从任何其他人的人”。这使得他发展自己的理论从批判奥斯丁的理论开始。
按照我们对哈特论证的一般理解,哈特首先按照奥斯丁的主权者命令说(the prescription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构想了一个简单的雷克斯法律世界(CL, 54)。然后哈特又指出,这个只有服从习惯的法律世界无法确保法律的连续性(continuity),除非引入某些规则,比如关于王位继承的规则,而连续性是我们熟知的任何法律体系的特性。最后,哈特指出,社会单纯拥有一种习惯和拥有一项规则的差别在哪里。
原始论述
尽管哈特明确说自己按照主权者命令说构想了一个简单的雷克斯法律世界,但这不是发生在他开始构造这个世界的一开始。让我们一点点看哈特的论述。
一开始,他就指出,“服从”这个词本身暗示了对权威的遵从,而不是仅仅是对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的服从。因此服从的行为一定涉及某些规则,以表明在怎样的情形的联系之中,人们算是服从。比如,对服从的描述至少涉及一个条件句所表达的情形:如果被服从者如何言行,则服从者如何言行。这是一个不只是只被观察者描述的规律事实,还是一个当事人需要明确掌握的一项规则,比如对于服从者来说,这个规则可能是:“如果他做了什么,那么我应当做什么。”
然而哈特转头说,就他当前的论述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相当简单的例子,人们也会承认在这个例子里,“习惯”和“服从”等语词得到了明显的应用。
他设想有一群人长期生活在由专制君主雷克斯统治的领土(there is a population living in a territory in which an absolute monarch (Rex) reigns for a very long time),雷克斯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来管理他的臣民。
在这之后,哈特紧急着说,很难认为,这样的服从属于“习惯”或者说“习惯性的”(CL, 52)。对雷克斯的服从“缺少习惯这个要素”(CL, 52)。然后他说,尽管如此,它包含其他重要的要素。他举人们早餐看报纸为例:人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一直这么做,并且极有可能未来还会重复这样做。(CL, 52)“如果是这样,在我们想象的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动乱初期的任何时候,一般地服从雷克斯的命令并且很可能继续这样做”。不清楚的是,这里的“如果是这样”(If so)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后面会明白,这意思就是我们远退当一个旁观者确实会观察到重复行为(无论被观察的社会现象内部充满如何复杂的观念和规则)。
接着下一段,他就开始明确说雷克斯社会“有服从习惯”,“服从的习惯是雷克斯和每一个臣民之间的个人关系”,每一个臣民都习惯服从雷克斯的命令,就像每一个人习惯周六晚上去酒馆一样。(CL, 52)再一次地,现在哈特引领读者一起站在雷克斯社会之外观察。
在这之后,哈特又说,“明显,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在字面上使用服从习惯的概念(the notion of a habit of obedience)”(CL, 53),然后他又说,这样一个社会因为过于简单可能“从未在任何地方存在过”(CL, 53),它也不是一个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中不会有雷克斯这样的专制统治者。(CL, 53)
尽管如此,哈特又说,雷克斯治下的社会有一些与受到法律管理的社会相同的标志,至少在雷克斯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所有成员服从一个相同的人所构成的统一”,“即使这些人对于这样做的正当性没有什么观点(views)”(CL, 53)。
宽容解读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简单的雷克斯法法律世界到底能够上存在呢?哪怕在概念上的,也就是我们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字面使用“服从”和“习惯”得到的概念的?哈特闪烁其词。他一开始就说,服从的社会活动不可能没有任何观点,或不涉及任何规则。但是他还是努力去设想一个简单例子,说这里有服从习惯,没有任何观点,没有任何规则。等他设想完了之后,他马上又说这样的社会太简单以至于从未存在过。他的意思是,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社会,但他设想的可能在概念上存在。
一旦你仔细思考,服从的行为怎么可能是无观点的?按照哈特的行文,他自己都不相信是这样。
一个试金石问题是,哈特说这个简单的法律世界中,服从的习惯是建立在每一个臣民和雷克斯个人之间的。这令人匪夷所思。怎么可以设想一个政治社会,其中每个人单独地和一个相同的人的建立个人关系,哪怕是任何类型的关系?
哈特所以这么设计情节,无非是想要屏蔽雷克斯社会中服从活动中的任何概括性观念(或者你愿意说,抽象观念)。哈特能设想一群人能够汇聚起来且能建立哪怕最简单的统治关系,却认为人们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概括性观念,有可能不把雷克斯视为某种概念的承载者。然而哪怕在最原始的社会,年长者(我不愿意说“长老”,因为它已经是个含义如此丰富的概括性词汇)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被视为某种概念的承载者,比如“有智慧的人”“通灵者”。甚至每一个人眼中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许许多多的观念(notion)的承载者,哪怕是当用到“妈妈”这个词时。
没有“国王”“统治者”“领导者”诸如此类的无论什么概括性观念的雷克斯专制统治社会真的可能吗,哪怕仅仅是在概念上?思想或谈论这些事情本身就需要这些概念,开展这些实践又怎么会没有?人类的服从行为真的可以是毫无观点,纯粹习惯的?只有幼鸭跟随母鸭的行为可以是这样(并且鸭子只能被我们用“服从”“习惯”来形容,而不能自己使用这些词)。
现在让我们假设,雷克斯社会的所有臣民和雷克斯本人没有任何相关的概括性观念而建立了服从和统治的单纯的习惯,就像雏鸭刚睁开眼看到母鸭或者任何移动的物体而跟随一样,但只要他们社会是人而不是动物,就必定观察到以下事实:
(1)我个人服从雷克斯;
(2)他们也个人地服从雷克斯。
这两个事实,在雷克斯的社会,至少在小范围内,且有多个小范围组成的普遍范围内,被个人之间相互知晓。这种相互知晓的事实,一定会改变他们每个人看待雷克斯个人的观点,雷克斯不能(谁也无法阻止,包括雷克斯臣民和雷克斯本人)只是单纯的个人了,而必须是一种东西:雷克斯是比如说在我们的观念中的“王”或者最简单的“优越者”(被每个人服从的事实就足以让每个人不可能避免地有这个概念,无论人们是否清楚到底是什么优越。德行?武力?身高?在所不问)。
因此,即使采取最最最宽容的理解,即使服从雷克斯的行为仅仅是一对一的,且服从建立自始至终不需要规范性的理由,不需要对雷克斯有任何观点(无论是物理的还是价值的),但是只要这个故事的主角们还是人而不是一群鸭子,这个单纯的普遍服从事实就一定会让人们产生对雷克斯的概括性观念,即使上帝也无法阻止,否则他就没有造人。雷克斯必将被视为某个概念承载者,哪怕这个概念的承载者仅此一个。
如果不是那么宽容的理解,那么上面的那个事实(1)本身必须要有一个规则,为了使得至少每个人臣民正确实施服从行为,得掌握一个规则:
若雷克斯做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
或者如果你觉得这里的“应当”有规范性暗示,那么:
若雷克斯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这边会发生什么情况。
哪怕把“应当”去掉,把“服从”关系完全变成一组附随事实关系,规则都必须被掌握,这里必须包含类型的认知,“他若如此这般,则我如此那般”,否则所谓的服从就是各做各的。
更不用说雷克斯那边的观念的变化,以及如此普遍服从的建立所要服务的社会目的。没有这些社会目的,这种服从习惯的建立的意义也许只有鸭子能回答了。只要有目的,对雷克斯的服从一定是事先建立在某种观点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哪怕仅仅是从概念上,人类都无法设想一个只有服从习惯的雷克斯社会。暗中用一系列概念——王、臣民、社会、服从、统治、专制设想一个没有这些概念的社会现象,就像是说“我没有说话,包括这句话”一样地荒诞。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无法设想是不是恰好就是哈特所要证明的呢?因此他的例子更应该被看作论证上的归谬,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一个人类学假设?到底是哪种情况,决定了简单的雷克斯法律世界(雷克斯一世时期)到复杂法律世界(雷克斯二世时期)之间的叙事性质,其中的变化到底是论证上的还是事实上的?我说的“论证上的”指的是,事实不是如此,但为了表明其中的情况是 A,先假设是情况是-A, 然后表明-A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而必须是情况 A;而“事实上的”指的是,至少事实的某一阶段就是-A,然后描述-A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而必须发展到 A。
的确如此,雷克斯社会的例子让很多读者觉得它是一个法律发生学故事:一开始雷克斯一世时没有任何规则,却能够有最简单的法律,但因为真正和成熟的法律必须确保持续性和连续性,到了雷克斯二世引入了规则(王位继承规则)。哈特的雷克斯社会在用一个人类学想象来论证法律的发生学:人类可能从一个无规则的不成熟法律社会发展到一个有规则的成熟法律社会!
但这恐怕连哈特自己也不相信吧?作为读者,要十分小心分清这点。哈特说:“应当注意到,在这一极为简单的情形中,共同体要确立雷克斯为主权者,所需的一切仅在于民众各自作出服从的个人行为。就其个人而言,每个人只需服从即可;而且,只要服从是持续且稳定地作出的,共同体中便无人需要对自己或他人对雷克斯的服从是否在任何意义上为正当的、恰当的或合法要求的,持有或表达任何看法。”(CL, 53)要记住,这句话之后他就说,“这样的社会从未在任何地方存在过”(CL, 53)。
他谈到了雷克斯一世死后,那个社会出现了“继承时刻”,雷克斯社会要在那个时刻不间断有法律,光靠习惯是不行的,因为对雷克斯二世的服从习惯不能立刻建立,除非引入“继承”“资格”“立法”“权利”等概念。引入这些要素之后,就无法用服从习惯的语言来说明了。但是紧接着,哈特又说:
“我们从这个角度,依照主权理论的方法,构想了简单的雷克斯一世法律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权利或资格,因此更不用说没有继承之权利或资格了:那里只有这样的事实,即雷克斯一世下达了命令,而他的命令习惯地获得服从。就在雷克斯有生之年,将之构成主权者,并且使其命令成为法律而言,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样并不足以说明其继承者之权利。”(CL, 54)
哈特最后说,在“继承时刻”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因为不能被服从习惯所满足,使得雷克斯二世的法律世界理解建立不可能;要是这样的,必须雷克斯一世统治期间,就确立了某些规则,不是单纯的习惯,因此也就有更为复杂的一般性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对规则的接受的实践,尤其是授予新立法者继承资格的规则。紧急着哈特就转向论述规则和习惯的差别了。(CL, 54-5)
怎么理解雷克斯社会的故事的这个结局?也许哈特是想说,即使“继承时刻”没有发生继承,依照主权者命令理论,至少有一个简单的雷克斯一世法律世界;还是说,作为一种逻辑归谬,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把雷克斯二世的世界视为有法律的,那么雷克斯一世的世界就必须被认为是已有规则的。从上面我们刚才引用的段落里,确实有这个意思。
让我们假定是这样一个结局。这个结局说的是:没有规则的雷克斯一世的法律世界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可能是不是依照主权者命令理论不可能,还是绝对的理论上或概念上不可能。仔细阅读哈特的原文,他本来应该正确呈现出自己的论证的,但是他混淆了,他在归谬的过程中把雷克斯一世世界说成是没有用规则的,而不是没有规则的内在面向的。
什么意思呢?仔细阅读哈特在这个假象情形之后对规则和习惯的描述(CL, 55-6),特别是对其中涉及的规则的内在面向的论证,就可以明白。一个社会习惯和一个拥有规则的社会实践不同的不是是否依规则行事(在最一般意义的谈到的规则,例如操作流程),而在于对所依规则的反思批判态度,即不但实际依规则行事、明白意识到普遍依规则行为(你捕捉到自己处于一个社会习惯当中,就一定会捕捉到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接受这项规则,把这项规则用于自己的行为指引和批评他人行为的理由,以及相应地,其他人会一般接受以此为理由的批评为恰当的。如果我们仅仅是依规则行事而开展一种社会实践, 但若有人偏离,也不会遭到什么人的反对,自己也感受不到什么压力,那么就尽管有规则,却没有对规则的内在面向。
我现在已经尽最大宽容原则来理解哈特的主张。如果这些理解是对的,那么哈特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1)他要归谬的雷克斯一世世界不是没有对规则的内在面相,而是没有规则。
(2)他错误地把“接受规则”这一实践的内在面向错误表述为规则的内在面向。
(3)他所以烦第(2)个错误,就在于他第(1)错误的归谬,把一个本身就不但有规则且有对规则接受的事实才可能有的社会现象处理成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现象,他把对社会实践的观察视角的变化处理成社会现象类型的变化。
现在已经很明白,第(1)点错误已经表明,哈特只能归谬不可能有无规则的法律世界,而不能归谬奥斯丁的主权者命令世界是一个无规则的世界。也就是说,雷克斯一世世界不只是在命令者理论上不可能,而是在任何理论上不可能。
三个问题
下面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我们前面的三个初步结论,第一,明确雷克斯社会是在理论上不可能还是只在主权者命令理论上不可能;第二,指出哈特完全忽略奥斯丁自己对“服从习惯”的使用;第三,表明哈特在这个论证中犯下的范畴错误,把视角转换看作事物变化。
雷克斯社会是在理论上不可能还是只在主权者命令理论上不可能
我们上面的讨论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点。没有任何概括性观念,我们自己甚至不能思想,何况一个社会服从的产生?没有任何概括性观念,我们自己甚至不能思想,何况描述一个社会服从?何况描述一个被称之为法律世界的社会服从世界?既然认为“服从”哪怕从字面讲也包含了规则要素,怎么又能设想一个“字面上”应用这个词的无规则的情形?这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就好比你已经知道,逻辑上不可能有 a 这个前提,但你还是假设若一个推理有这样一个前。然后你做的事情,当然,是推翻它能够是前提的假设,但这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归谬法。
“服从”不能只是个被我们从外部观察的人使用的词,因而我们可以只观察和报告:“看那个社会的人们,每当某个人发布命令,他们就照做!”我们也必须允许我们观察的社会中的人们使用。当社会实践内部的人使用“服从”这个词时,怎么可能设想“他们”(这已经是我们设身处地)在一种与规则无涉的意义上使用它?
我们知道,温奇对哈特有一定的影响。温奇在《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1958 年)中追随维特根斯坦关于思想和实践的一个洞见,指出任何概念以及任何实践都是规则支配的。你不可能不使用任何规则而拥有一个概念。比如,你想拥有一个苹果概念,你得有至少这样粗略的规则:如果一个东西是看起来尝起来如此这般,那么它是苹果。规则构成你聚焦世界获取对象的约束条件。至于实践,首先最经典的能称之为实践的宇宙活动,都必须使用概念的,因为实践是带着理解的人类活动,其中包含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生活的目的。
温奇警告说,社会学家假如认为自己的确研究的是实践而不是与实践无关的自然事实,那么实践者的自我理解一定是要注意到的。这里温奇不否认,社会学家确实可以做到仅仅把一个社会实践的外部可观察的规律性事实、模式观察和记录下来。由此获取的社会事实仅仅是社会实践的外部面向,它不是不属于社会实践,只是不能等同于社会实践。就像他指出的,如果你打算说明一种宗教活动,你不能仅仅从外部描述它所呈现的出的人的行为的模式或特征,而是还要去关心这些信徒对自己的实践的理解,否则你就不是在说明一种宗教社会实践。
哈特应该熟悉温奇的这套观点,他的“规则的内在面向”亦是对这种思想的重申,但是他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实践的内在面向”理解成“规则的内在面向”,把从外部观察获得的社会事实(社会习惯)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现象类型,即无规则支配的社会现象,而把那些有规则支配的社会现象视为另一个独立的现象类型,并且更愿意称之为实践,他把按照温奇理论可区分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规则、习惯这两种面向看作拥有规则和只有习惯的这两种实践类型。
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话,如果哈特只是在归谬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法律实践,那么既然依照任何理论也根本没法设想雷克斯一世法律世界,依照主权者理论也根本没法设想雷克斯一世法律世界。雷克斯一世法律世界例子和其所用于的论证的自我挫败不是主权者命令理论的失败。
奥斯丁自己对“服从习惯”的实际使用
虽然一再小心辨析“服从习惯”的使用,哈特表现得从未读过奥斯丁的书一样。这真是哲学史上最大的“莫须有”栽赃。作为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成员,哈特应该不会不懂一个道理,不要盯着别人使用的语词固有的意义不放,而是要看他实际上用这个词做什么。即使奥斯丁使用“服从习惯”,我们也要看他用来指什么或做什么。作为熟悉语言哲学的哲学家,哈特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竟然完全抛开他所批评的对象对语词的实际使用,而单纯考察语词固有的用法或含义(而不是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或观念的固有的内涵,哈特没有犯这个错误,但他的读者就不一定分得清了)。语言哲学家已经告诫概念要用语言来表达,但重要的不是语词表达的概念的固有意义(因为根本没有所谓固有意义),而是语词被实际使用的方式。从他的表述看,他一直在考察的是“我们”会怎么使用“服从”“习惯”这些词,因此他竟然相信任何词可以自身有客观的、固有的被使用的方式,而从未考虑奥斯丁是怎么使用这些词的!
在奥斯丁的文本中,“服从习惯”强调的是长期性、连续性的服从事实,比如偶尔的不服从不会中断统治关系。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大量笔墨讨论“服从习惯”问题的部分在第六讲“政治社会的起源或缘由”,这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驳斥社会契约论而推崇功利主义者道德学说。奥斯丁追随边沁(边沁在《政府片论》里说:“习惯是行为的总和,目前,我把那些自愿的克制态度也包括在这个名称之下。因此,服从习惯就是服从行为的总和。”这里的“服从习惯”其实就是对于政治社会统治现象的一个称呼,并表明其内部的原因或理由以及规则有待考察而已。中文版第 134 页脚注),共同反对社会契约论(由于它与自然法理论有亲缘关系而反与功利主义学说不对付),在他看来,依照社会契约论,政治统治能够依照一个契约突然形成,也会突然结束,但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社会的统治者被服从的事实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历史性的过程。相对于“签订契约同意被统治”而言,奥斯丁和边沁使用了“习惯的服从”的表述,“服从的时间,究竟需要多长,才能使这种服从成为一种习惯的服从?”“如果服从同一优势者的人数,是十分众多的,服从次数,是十分频繁的,而且持续不断,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迟疑地宣布它是政治性质的社会”。(p.254)
“服从习惯”或“习惯地服从”的使用,绝不是被用来表示,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关系是没有任何规则或观点的(哈特的第(1)个错误,也不是用来表示,没有所谓的规则的内在面向(我们应当正确称之为“对规则的接受态度”或“实践的内在面向”))。请看奥斯丁的一些论述:
首先,关于服从习惯,他说,在所有的独立政治社会,都存在主权者习惯遵守的原则或准则,而且这些原则或准则,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或者至少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赞许的。主权者时常明确表示遵循它们,并实际上习惯遵循它们。但这些原则或准则,仅仅是道德上的。因为当主权者贸然违反这些原则或准则, 不会遭受任何法律上的痛苦或者说惩罚,尽管会遭到被统治阶层的谴责甚至抵制。这些明显的关于人们对规则的态度的讨论,既不能被用于说明奥斯丁的法律世界没有规则,也不能被表明奥斯丁的法律世界没有对规则的接受。
其次,关于君主统治,奥斯丁说,人们很早就认为,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君主统治,古罗马的任何皇帝都不是主权权力的唯一掌握者,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真实社会,最高统治都是若干人的统治。任何实际的君主个体,总是受制于君主所在的阶层的舆论或道德感觉。他特别强调,君主立宪政体不是君主统治,而是无数贵族统治形式之一,其中有无数主权成员分享主权权力。人们有时会把一人专制君主统治看成是一人统治,这是没有认识到那个具体的个人只是君主这个位置的占据者而已。
再次,奥斯丁甚至还提到“国王得永生”(the king never die)的英国谚语。他说:“关于这一宪法的一句格言,可以说明这一段落的主题。这句格言是:‘国王得永生’(the king never die)。我相信,其含义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尽管王位上的端坐者。是具体的个人,终有一日离开人间,其生命是短暂的。但是,王位本身的延续,是不可能中断的。……当一名真实的国王去世的时候,王位可以立即传给符合国王一般特征的要求的具体个人,这个人,有资格戴上皇冠。”根据《王位继承法》所描述的国王的一般特征,这名具体的个人,是皇冠的继承者。(p188-189)他在许多地方明确指出,主权者、国王、皇帝等等无论什么统治者的称呼表达的是一个资格、政治位置,是具有特定特征的人,而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乔治成为英国的国王,以及爱尔兰的国王,成为最高主权机构的特定的实体的一名成员,不是因为他是具体的乔治,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符合国王的一般特性的个人”(p187),“最高统治实体中的成员,是根据一般的和固定的资格,来掌握最高统治地位的”(p194-5)。
已经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奥斯丁对“服从”“习惯”以及与之相关的“主权者”的使用不是偶见于文本,而是系统地明白地使用,只有不读奥斯丁的书的人才会认为奥斯丁笔下的国王可能是一个鸭子王国。
总之,奥斯丁的“服从习惯”还直接继承边沁的用法,和边沁一样,这个短语被用于与社会契约论划清界限用的,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的建立是缓慢的和历史的事实,而不是突然的契约签订。
无法否认,哈特在做一个完全与奥斯丁的理论完全无关的稻草人论证。
视角转换和类型变换
现在我们来到哈特关于社会习惯和社会规则(一种特殊实践)的社会现象类型区。他的错误隐藏很深,他要说明的是一个社会“拥有一项规则”(have a rule)意味着对“接受规则”(rules-acceptance)的反思批判态度,但他在雷克斯设想情形中对比论证的是,无规则的社会现象和有规则的社会现象。因此哈特的错误有两个不同层次:他的第一层错误在于:认为有无规则的社会现象和有规则的社会现象这两类社会现象;他的第二层错误在于:认为有对规则没有内在观点的社会现象和对规则有内在观点的社会现象这两类社会现象。第一层中的前者都叫习惯,第二层次的前者都叫社会规则(实践)(他在这一点上是模糊的,他只是对照的是“习惯”和“拥有规则的实践”,但他也在实践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规则”,因此我们不能说哈特拒绝习惯是一种实践。)。
下面我们将证明,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哈特的论证都犯了一个范畴错误,把视角转换看成类型的变换。
任何一种不算是琐碎的意义上的社会现象,都是规则支配的(rules-governed)。当我们观察到一群人周六都去一个酒馆喝酒,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规律性行为的现象,并且能够预测。这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习惯案例。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依什么规则这样做或者对规则有什么态度。
但是设想,如果我们深入人群之中,和他们交谈,可能发现他们每周六来举办一个重要的艺术沙龙,或者发现他们是情谊深厚的老战友。对于他们来说,“我应当每周六去酒馆做那件重要的事情”是明确的规则,且是接受的态度。实际上,只要足够接近这群人,这些事实必定逐步向观察者显现。只有设想仅仅从酒馆对面的比咖啡馆静静地看着他们每周六进入进出酒馆,我们才说他们有一个习惯。但是,当我们说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能够否认他们对自己的实践没有什么观点和规则吗?
哈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把视角转换看成是事物类型的变化。它的论证具有归谬论证的表现,因为只要他谈论任何的社会活动,总是有规则支配,不但是社会活动本身有规则支配,而是任何对于社会规则的谈论也是有规则支配的。所以当他从设想无规则支配到有规则支配,我们觉得很有常识感,而略忽略了他论证中的混乱和逻辑错误。
不是一个社会实践没有规则,而是你从外部描述的时候看不到它内部的规则。不是一个社会实践没有对规则的接受,而是你从外部描述的时候看不到它内部的规则接受。
他的论证的常识感得自于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复杂的社会实践是不依规则行事。习惯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实践类型,而是对一个社会实践的视角。这就好比,哈特说,任何苹果都不可能只有果皮;假设一个苹果只有果皮,我们会发现它们不可能得到支撑,结论是它实际也有果肉。当然如此!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但仍然有可能只看到苹果的果皮,并且在这个时候,你注定看不到果肉。但是他把他看到的只有果皮的“苹果”视为一个独立的苹果种类,而其实这个“苹果”不是所有苹果的一种视角。但这里没有类型的差别,也没有发生学的变化,只有视角的变化。
让我们稍微回顾下之前对他的例子中魔法发生的地方。在小心略过所有这些犹豫之后,他的设想依赖于这样一个对比:即使承认有服从但没习惯要素时,但我们设想我们能够观察到雷克斯的臣民过去很久以来服从雷克斯,并且未来仍有极大可能重复之前的服从行为;正如我们观察到一群人过去很有以来周六晚上去酒馆喝酒,并且未来很可能继续重复之前的行为。这二者的相同之处是,都能从外部看到行为的重复和未来继续重复的可能性,也就是发现一种行为的规律性(有过去和未来时间面向)。最后,哈特做了一个“逻辑魔法”,因为去酒馆喝酒是一个典型的习惯,并与雷克斯社会有类似的情形,因为也可以认为他们的服从行为是一种习惯。
哈特的魔法是什么?喝酒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因此我们如果假设服从雷克斯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鉴于它们之间其他要素的相似——外部观察到的行为的规律性——因此如果去酒馆喝酒的确是一个习惯,那么服从雷克斯也可以是一个习惯。
哈特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依照我们对“服从”的最宽容的理解,都无法想象服从的行为是一个习惯(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去酒馆喝酒是一个习惯)。他也承认这一点。他暗中引领读者设想自己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来观察整个雷克斯社会的情况,就像设想我们在街角从观察某个街道的人一样,看到了他们服从雷克斯的现象,并且这个现象过去重复了很久,并且未来有极大可能会重复,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观察的话。魔法生效,雷克斯社会有了服从习惯!习惯是什么?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特别的观点(这个“没有特别的观点”指的不是没有任何观点,而是正如哈特指出的,没有接受的反思批判态度的那种观点)。当你把目光拉远,把视角切换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视角,去看任何他人的社会行为,都可以是无观点的,无规则的,因而都像是一个习惯。这就是哈特在雷克斯的故事里所做的事情。
或许哈特愿意承认,他在第一个层次确实犯了错误,但否认自己在第二个层次上有错:“好,我承认,社会习惯确实经常只是一种视角问题,一个有规则且接受规则的社会现象会可能会旁观者观察和报告为一种社会习惯;但是,确实有虽由规则支配但不接受规则的社会现象类型,我们称之为社会习惯,我强调的是这个方面的差别。”
那么这些习惯是什么呢?首先,用第一人称,我们经常会对别人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开车的时候喜欢开着音乐”,也许我们恰好只是想让对方站在一个纯粹旁观者的角度看待我们的行为,不需要他的深入参与。如果他是你更好的朋友,或者如果发生了一个问题,必须解释你这样做的动机或目的或任何意义时,你可能会告诉他:“这是我前女友生前最爱的一首歌。”
用第一人称,我们有时候也会对一个陌生的或不太熟悉的人说,“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习惯,就是男士见到女士进门要起身脱帽”。你的姿态和上面的类似,恰好只是想让对方站在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视角看待你们的行为,或者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或者是一种不便展现自身实践的价值的姿态,动机有很多。但是如果他要加入你们,你的姿态将是尽可能让他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其中的意义,把握其中的规则。
用第三人称,我们可以把任何社会的任何一群人或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及其组合看成是一种习惯。我们说那个人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当然,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许有。这些是琐碎的,对于哲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这里的关键是,社会现象的个别化原则。什么是一个社会现象?我每周三去上课,我所在城市的一个姓马的人家都要做一顿红烧肉,并且与此同时,我的城市上空都要飞过春秋航空的9C5869 航班。这些事实一起构成一个社会现象吗?社会现象的个别化看起来是可以任意的,但一个有意义的个别化原则,应当是最终落实到一个社会实践,即规则支配的。如果我们把上述事实合并成一个社会现象,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其实不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不同部分,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由相同的规则支配,或者它们之间就没有规则。只有落实为社会实践的社会现象才是有意义的,而不以社会实践为约束的社会现象是任意的,以至于“我每次呼吸,太阳都在发热”可以构成一个社会现象了,而谈论这个社会现象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捕捉到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现象,经过研究落实到一个社会实践,捕捉的框架恰恰是规则本身,而且越有时意义的现象,越是可能接受规则的现象,只是可能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深沉、重大的社会实践的成员的确可能缺乏对其规则的明白的观点。这一点似乎构成对哈特的一个极大赞助:假设一个像雷克斯那样的社会,是建立在蒙昧的传统习惯之上的,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他们不是无规则,而是没意识自己在依规则行事。但是,这里就是人类学家该发言的时候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对这种远不是琐碎而是重大的社会实践有这样一种描述时,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来离得太远。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厚重的信仰、价值、承诺,虽然依规则行事,但并不是一定明白地依规则行事。这是另一篇文章所要单独解决的问题了。
结论
我们揭示了哈特论证的双重错误结构。在第一个层次,哈特错误地认为存在“无规则的社会现象”和“有规则的社会现象”两种类型;在第二个层次,他错误地认为存在“有规则但无内在观点”和“有规则且有内在观点”两种类型。这两个层次的错误交织在一起:哈特应该论证的是第二层问题,但他实际论证的是第一层问题,然后把第一层的结论(需要规则)偷换成第二层的结论(需要反思批判态度)。
这两个层次的错误有一个共同根源:哈特把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误认为观察对象的变化。习惯不是独立的社会现象类型,而是对社会实践的外部观察视角。从外部看到习惯,从内部看到规则和规范性承诺,这是同一实践的不同观察方式,不是两种不同的实践。哈特把自己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视角转换,误认为是实践本身从无规则到有规则、从无规范性到有规范性的发展。
本文标题“论哈特对奥斯丁的栽赃”是对这个哲学错误的准确描述。栽赃有三个层面:认识论的栽赃——把“看不到规则”误认为“没有规则”并强加给奥斯丁;本体论的栽赃——把“习惯”这个虚假的独立类型强加给奥斯丁;方法论的栽赃——哈特作为日常语言哲学家,却在批评奥斯丁时违背了自己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不看奥斯丁如何实际使用“习惯性服从”,而是盯着词的字面含义来曲解奥斯丁。这不是无知导致的误读,而是在明知正确方法的情况下选择错误方法。
有人可能为哈特辩护说,他批判的不是奥斯丁个人理论(CL, 18),而是一种“用纯事实说明法律”的理论倾向。但这个辩护不成立。第一,“用纯事实说明法律”在概念上不可能——任何“说明”都必须使用概括性观念,而使用概念本身就预设了规则。第二,奥斯丁根本不属于那个倾向——他使用“习惯性服从”是为了反对社会契约论、推崇功利主义,这本身就是规范性的理论工作。我将在别的地方正面讨论奥斯丁的真实理论规划。